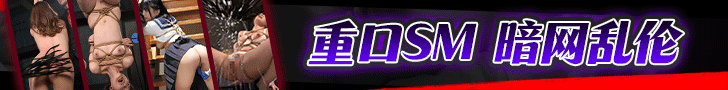“这是哪儿?”我问。
“我的实验室。”
“实验室?为什么我在里面。”我走到铁门前,推了推,无法推动。
“先生您要干什么?”我有点急了,用力地拉铁门,上面的把手已经有些锈了,我感受到了皮肤被扎破的疼痛,但我对未知的恐惧大过于此,导致丝毫感受不到疼痛。
我近乎疯狂地拉动铁门,在第一次用力失败后,我就知道这是徒劳的,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举动能减轻我恐惧的举动,或许是他笑着说这只是个玩笑?
他见我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,笑了起来,比我见到的以往他的笑容都更灿烂,嚣张,疯狂。
“别怕,只是对你做一个小小的实验,别执着于那扇门了,手上留疤就不好看了。”
他说完见我冷静了下来,打开了铁门,站在门口,看了我一会儿,好像在测试我的信服度,然后阖上门,对我注射一剂不知道是什么的药剂,趁着他准备其他注射液的时候我冲向铁门,我看到了自由,它躲在一个男人身后,这个随从像是毫不意外我会跑出来,单是用健壮的身体就挡住了我的去路。
“跑什么呢。”后面传来叹息的声音“好好适应吧。”
我无法通过自己知道时间,但是从他们送三餐的时间来看,我大概已经被囚在这个地方一个月了。我能感受到他每天都重复打的那针药剂的效果,我好像不再长高了,前段时间因为发育而带来的疼痛也消失不见,还有一个早起的现象也逐渐消退,直到最近已经不出现了,还有我瘦到胸骨突出的身体,我渐渐无法摸到那些骨头了。
未知带来的恐惧是顶级的,我察觉到了不对劲,问他还有多久能做完实验,他说看我的身体适应的怎么样,就在今天,他终于说了一个明确的时间。
“下周就行了。”
我难掩欣喜,但也挡不住恐惧袭来,我不知道他最后一步实验会让我变成什么样,那些药剂让我觉得我正在像不属于自己的性别特征靠近。
终于,完成实验的这一天来了,他让我躺上一个台子,旁边的刀具看着很恐怖,他给我打了一剂药,我便无知无觉地昏睡过去了。
在这段时间里,我做了一个梦,我梦到少爷在四处找我,我看到他手里紧紧攥着的那块我还给他的蓝色宝石,我看到他失眠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夜,让我很不理解,我只是个贴身仆人而已,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。
然后我看到少爷在深夜落泪,便什么也说不出了,他眼底的星星都暗淡了,好像大海变成了深潭。
很多零碎的东西在我脑中闪过,然后我便醒了,我觉得我的脸很难受,想去触碰,但被人一把抓住手腕,我疑惑地看向他,却见他躲闪我的目光。
“现在先别碰,你的脸也做了实验。”
我懂了,点了点头。
在做完实验后,我被搬出了实验室,在一个并不朴素的屋子里,那位先生一直照顾我,我发现我的下半身也被做了实验,多了一条脆弱的缝隙,一碰就疼,我问先生怎么回事他说那是正常现象,会随着我的脸一起变好。
我自实验后便一直没见过我的脸整日被纱布包裹着,所以当先生提出要拆纱布时,我是有一丝解放的欣喜的。
然后,我看到了自己的脸,一张很漂亮的,一看就是女生的脸,我能控制着她动,但我始终觉得她并不属于我。
“用她做个表情吧。”先生扶着我的肩说。
我笑了一下,看到镜子里的身后
人怔住了,然后大笑起来,就像把我关进实验室时一样的笑容,他大声说:“成功了!”
在那次拆纱布过后,先生对我可以说是像对待珍宝,明明我还是那个从富豪家逃出的不称职的仆从,但他的态度就像是在对待永远热恋的爱人,细心询问我的感受,但有时会让我强行喜欢某样菜品。
我的自愈力还是不差的,约一周后,下方就基本没什么不适了,先生说走吧,我很高兴——终于能回小镇了,尽管我的脸和身体上的改动可能会导致某些后果,但现在我只觉得小镇那个地方没有缺点。
先生看到我满脸的欣喜,温和地问:“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就这么兴奋?”
他自从看到我改变后的脸,说话的语气都变得不一样了。
“不是回小镇吗?”我疑惑。
“不是,”他回答,“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
“实验后就能回去,这是您说的。”我有些恼怒。
“我没说过这种话,我只是说用你做个实验,也没说一完成就能放走你。”他淡淡回道。
我哑口无言。
要见的人家在宫殿,看着位高权重,让我有些不安。
“您来了,本来今天王爵都打算亲自拜访了呢。”大门旁身穿黑色服装的白发老人先朝先生鞠躬,然后是对我,说了一句“您回来了”,让我不知所措。
老人带着我们去到接待室,这里的一切都很高调,包括从门后走出来的人,金发,有和少爷一样的蓝色眼眸,只是这个人的颜色更浅。
“舍得回来了?”那个男人看着我,说了句莫名奇妙的话。
我还没问出口,先生就抢先回答了:“我们会分手的,在我踏出这儿的那一步起。”
我还是很困惑,看先生却见他眼眶通红,一副很快就要哭的模样,他察觉到我在看他,转过头,“我爱你,莉安。”说完突然凑近,很克制的一个吻,但让我不适,我猛地推开他,正要问他为什么突然这样做,他却跑了。
我看到那个金发王爵笑得开怀,说:“终于和那个窝囊废分手了,你可算回归明智了,我亲爱的妹妹。”
“你也终于属于我了。”他向我走来,眼底是一抹兽欲的红,我曾在少爷那儿见过。
我跑向门口,门却紧合着,那个人步步逼近,我像是预感到我将又会像布娃娃一样任人摆弄,但这次的对象不是温柔的少爷,眼前的人散发着危险的气息,让人不寒而栗。
“我不是你妹妹。”我手里拿着烛台,对着他说。
“你怎么会不是。”他还在步步紧逼。
“我是被他改造的人,我有和你一样的东西。”我指着身下。
“你不用为了躲避想这种拙劣的把戏,我会很温柔的。”
我用力把烛台砸向他,他接住放在一旁,“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。“
他把我扛起来丢到床上,那个言而无信的人实验前给我注射的药液让我不再发育,现在的身体不能再羸弱。
他扒下我贴身的衣物,怔愣住了。
“你是谁?”他的眉头狠狠蹙起,凶狠注视着我。
“我谁也不是,他利用我冒充您妹妹,我本来是个男孩。”我试图解释清楚,但他愤怒的脸上出现了玩味的表情,“听说双性人味道很不错。”
他又覆上我的身体,让我想到了少爷,少爷不会这样暴力的撕扯我的衣服。
可能是距离变远,也可能是太久没见,我想到少爷时不会再出现那种矛盾的情感,我甚至觉得相比起少爷,我前前后后遇到的人都没他好。
他撕扯的动作变大,我越发觉得恶心,用尽全力推开他,扯过被子包住身体,任指甲都因为被子的争夺而暴力脱落也不放手,血染上了被子和床单,我感觉到他争夺的力度消失,听见他狠狠放下一段话:“接受不了我,那就都去接受别人!”
这绝对不是好话,我可能会死。
听到他重重摔门的声音,我反而心安了,到窗边观察逃跑路线,见到围墙上都生长着荆棘,我却觉得相比那个王爵的狂躁,在上面踩几下可能是最简单的处刑。
我把床单系在床角,抛出窗户,抓着它滑下去。
本来我做这种事是很熟练的,但一个月的细养和实验让我的身体素质越发差,滑到一半时我突然失去了握力,摔到了地上,所幸下方是柔软的草坪,但骨头还是像错位一样疼。
我不知道路怎样走,这个地方繁华的像天堂,有穿着华丽的人走在街上,我只能用力跑出城。
我从来都是个野孩子,前不久才有了教养。以前我在街上晃荡,没事干的时候就喜欢去山上坐着,爬到最高的地方,能看得很远,于是我到处找山,走过草地,穿过林子,我的脚已经磨烂了,衣服也破了很多地方。
我爬上高山,前方有个小镇,不是我所熟悉的,但是我可以去问个方向。
我找到了一位中年的妇人,问她莱德思镇在哪儿,其实我并不是很确定小镇是否叫这个名字,
以前我在镇牌前经常看到几个字母,熟悉到可以画出来,但那时不识字,后来少爷教我认了字,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。
她面色变得有些奇怪,问我:“是说莱格斯镇吗?你要去那儿?”
“是的。”我点头。
她上下扫视我一遍,打量我一会儿,说:“那边可不安宁,你还是别去了,你去很容易被抓走。”
“被抓走?为什么?”
妇人凑近了我:“最近那个镇子里经常有小孩被抓走,大概就是你这个年纪,而且”她看着我的眼睛。
“据说都是灰色眼睛。”
我摸上眼睛,对她笑了笑:“您告诉我方向吧,我家人在那儿。”
“你往那个方向走,穿过一个森林,记住,一定要直着走,偏了会到另一个森林。”说着她递给我一根绳子。
我向她道过谢,走向那个森林,绳子在身后始终是直着的模样。
妇人没说大概的时间要耗多久,我只能不停地走,野果和溪水都能勉强填肚子,我的身上因为叶片多了很多条划痕,它们在溃烂,即使我经常用清水洗,它们也在逐渐扩大,就好像我这个人没有自愈的能力一样。
小镇的镇牌从来没有那样令人温暖过,上面是熟悉的字,其中一个被一团东西挡住了,我走过去的时候看了一样,先是惊诧,因为那是人的脑袋,再是不敢置信。
杰思敏?
那个管家?
为什么?
他连死的时候都是皱着眉的,我不解于他突然的死亡以及这个示威般的人头,我抓住一个人,问他:“被挂在镇牌上的人干什么了?”
那人正要解释,看向我眼睛时,却突然露出恐惧的表情。
他大声说:“这里有灰瞳!”
一堆人跑了过来,抓住我,把我放到一个破旧的马车上
我想到了那位妇人之前说的小镇里有很多灰色眼睛的人被抓走,但是无法再深想下去了,我觉得我的脑子好像堵住了,又晕又疼。
我被送向未知的地方,可是我才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不久,我还不想走。
在简陋的马车上的时候,我透过木材裂开的缝隙看到马车夫此时正在驾驶经过的地方——那个森林里被开了一条路,野蛮的开路,像是光凭车子多次的经过所导致。
车子停了,地方到了,我怔住了。
不是因为熟悉的建筑,不是因为路旁没有了漂亮的薰衣草,是因为我看到一个人。
“先生您看”马车夫边搓着手边笑的谄媚,“我给您带来一个灰瞳的漂亮小姐。”
少爷的脸上什么神采都没,他看了眼旁边的仆从,仆从会意,给马车夫一张钞票。
马车夫笑嘻嘻地接过,正要回头走,少爷却叫住了他:“等会儿。”
说完他走近了我,我看到他眯起了眼睛,端详着我。
应该是认不出来的,我的脸和性别都被改了,肯定认不出来。
“你回去吧。”少爷对马车夫说。
“你和我过来。”少爷对我说。
他叫来了家庭医生,帮我处理溃烂的伤口,发现我的体温不正常,我才得知我发烧了。
那个医生先生的脸色不怎么好看,几次张嘴又闭上了,少爷在随他走出房门前跟我说:“好好养病。”
我的脑子越来越堵,简单的思考都不能了,医生打的一剂药也只是起了一会儿作用,眩晕感铺天盖地地袭来,头一次觉得活着原来这么累,我感觉我好像下一秒就要去天堂了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好像丧失了时间的概念,少爷终于回来了,他坐在床边,问我:“年纪。”
我的喉咙被烧干了,干涩的疼:“不知道。”
“也是,你现在动脑都困难。”
然后少爷便走了。
我这一躺,一病,除了擦身子就没再起来过,家庭医生每天都来看我的状况,见到那些伤口久久不愈合,只叹息地摇摇头,有时我不解地看他,他会对我勉强地笑笑,安抚似地摸摸我的头。
被少爷安排来照顾我的女仆一开始是一副很嫌弃和不乐意的模样,这种表情会在我吃送来的饭菜时产生变化,变成渴望,我看她对美食有兴趣,正好有吃不下的菜,便把她招呼过来一起吃,当时她的表情显然是有些惊愕的,后来食物入口了又变成感激。
她叫埃文,是家里第三个女儿,她的父母本来以为前两个都是女孩儿,第三胎应该是个男孩了,在她出生前就定下了这个名字,后来发现是女孩,倒也没失望,让她抓阄抓名字,还是埃文。
在与埃文熟络前,我觉得整日躺床上十分无聊,但熟络后便不一样了。这个极其有趣的女孩,讲话很夸张,但不让人反感。她的碎碎念很亲切,我有力气的时候坐着听,她就会站在床边,有的时候表演很夸张的动作。我躺着听的时候她就坐在床沿讲。
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,有一次我要去擦身子,她看我身子这样羸弱,
走几步就面色发白,提议帮我擦身子,说这能促进情感,我只让她擦了后背,这么神经大条的女孩,居然擦的力度这么轻,我让她擦重点,她说:“密密麻麻好多伤,这怎么擦重。”说着还唠叨起我本来身体素质就差还不爱惜。
我的病越来越严重,这不是我自己发现的,是通过医生先生越来越深的皱眉发觉的,他对少爷说了,我才发现最近做起来的次数都少了,埃文在旁边轻轻握着我的手,温暖源源不断地传来
我开始失去坐起来的力气,抬手吃饭都累,咀嚼也累,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多,好像要就此深眠。
当我在一如既往的黑色梦境里时,我听到一声短促的尖叫,很大声,我睁开眼,发现是埃文,我的衣服被脱下了,埃文手里拿着毛巾,地上还有她倒退时踢翻的水盆的一滩水渍。
埃文捂着嘴,床头的暖灯照亮了她震惊而瞪大的双眼:“你怎么会有男性的器官?”
“我本来是男性。”我把被子盖上身体。
“你是做了什么手术吗?”
“嗯。”
她见我低着头不言语,把地上的水渍清理了,坐到床沿上,沉默一会儿后,抱紧了我。
“我们是朋友,我不会乱说的。”
我任她这样抱着,把头靠在她的肩上,直至天亮。
我可能是要死了,我看见医生先生对和他一起过来的少爷摇了摇头:“感染的太厉害了,什么药都没用,越猛的药越会消耗她的生命。”
少爷没什么表情,只是破例地在医生走后留了下来-以往他们都是一起来去的。
“少爷?”
“叫先生吧。”
“以后每天我都会多陪你一个中午,你好好休息。”他说完就走了。
少爷果然实现着诺言,每天中午都会过来,这种时候埃文就会出去,但她一出去,房间里就会变得很冷清了,我现在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了
有一个中午以往都只是应和的少爷突然主动提起了一个话题“我以前喜欢过一个男孩,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很漂亮我想着对他好,是不是就能让他和我一起待在这个令人烦躁的庄园里,但是他也觉得烦,他不喜欢这样的生活,把一个带有我们俩的名字的宝石礼物退了回来,我到处找他,找不到。但是我想的要疯了,不听从我父亲的劝说,拒绝父亲的联姻,拒绝他的建议,拒绝与人交流,我那个可怜又脆弱的父亲居然就这样气死了。”少爷说到这时笑了一下,但是无法让人看出高兴。
“我把那个在葬礼上还在指责我的老头管家给杀了,太吵了,我那时起可能就有点疯掉了。很神奇对吧,因为一个人我变成现在这幅样子,但是我居然难以对他怪罪,甚至还想见他一面,如果可以,就得寸进尺地抱他一下。”他的嘴角扬起来了,看着窗外的眼睛里有细碎的阳光的反射。
我听他讲着熟悉又陌生的事迹,看这个近在咫尺的人终于露出我熟悉的一面,明明是要高兴的,但我越来越困了,好像下一秒就要把头砸在床上。
我要是这次睡着了,可能就见不到他了。我突然产生了这种想法。
“很不好意思治不了您的病,把您带过来可能是错误的,但当时觉得您的眼睛”他顿了一下。
“太像他了。”
我努力睁大眼睛,我要看不清他了,但还是努力回答他:“兰德曼吗?”
他的眼睛突然就睁大了,抓住我的胳膊:“你认识他?”
“我就是他。”
太困了。
我先睡了。
少爷再见。